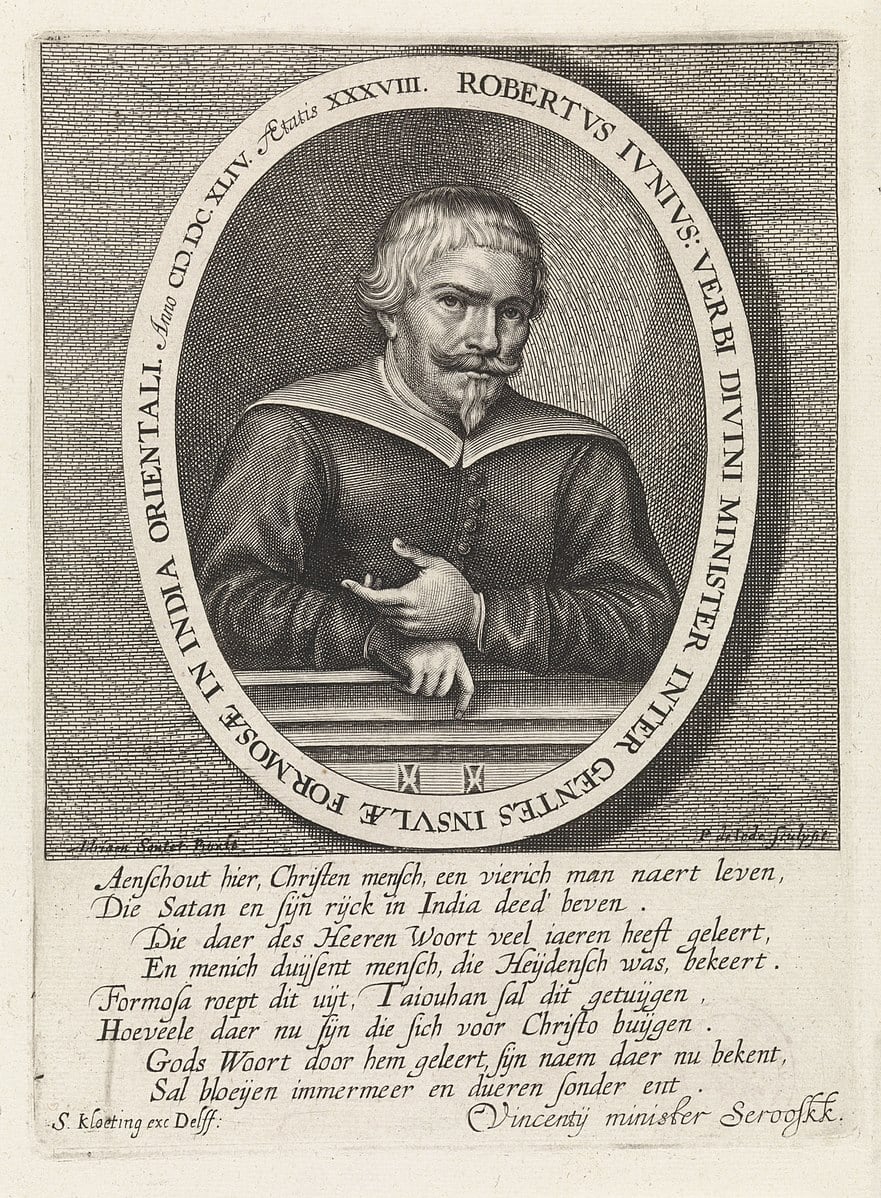Chapter 2
島的多種真實
(17世紀前)
《番社采風圖》記錄了 18 世紀清帝國眼中的臺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,也是後人研究平埔原住民歷史的重要依據。
「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,居彭湖外洋海島中......。斷續凡千餘里,種類甚蕃。別為社,社或千人、或五六百,無酋長,子女多者眾雄之,聽其號令。......男子剪髮,留數寸,披垂,女子則否。男子穿耳,女子斷齒,以為飾也。地多竹,大數拱,長十丈。伐竹搆屋,茨以茅,廣長數雉。族又共屋,一區稍大,曰公廨;少壯未娶者,曹居之。議事必於公廨,調發易也。」
“
”
1603 年 1 月,福州人陳第隨征剿倭寇的沈有容軍隊渡海來臺。
他這趟行程前後僅二十多天,所見僅大員灣(今臺南安平)一帶居民,寫成〈東番記〉一千四百多字,如今卻是早期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,經常被放大到近乎代稱 16 、 17 世紀之交的臺灣原住民世界。
如同列舉的原住民畫作一樣,它們固然留下了珍貴的紀錄,但終究是來自外人的視角。
如今我們稱為 1603 的那一年,在線性歷史裡有個位置,但在多數未發展出文字曆法的臺灣原住民看來,這一年、那一年、每一年,大概都只是模糊的時間背景。
在當時當地原住民的記憶裡,沈有容驅逐倭寇有可能被視為「兩群有大船的人在潟湖爭鬥」的事件。
事件本身不見得很要緊,但在一定的人身經驗限度內,或可作為一種時間標記,例如「颱風特別嚴重的那個夏天」或「北邊的人偷襲我們的那個新月」,在口傳裡短暫留痕,然後隨一代人逝去而歸於塵土。
以文字記載為基礎的文明歷史觀,和以人身經驗為基準的原住民口述傳統,是兩種悖反的世界觀。
這意味著將原住民納入歷史的敘事框架,所得往往是「原住民相關的臺灣史」,不見得就撰述了從原住民觀點出發的原住民史。
真正的臺灣原住民史觀才剛起步,發展與實踐都需要時間,我們無法現在就提出理想的敘事,但我們試圖在此突顯這道尚待跨越的鴻溝,並指出可能的整合方向。
究竟從何做起呢?
也許我們得先將目光自今日備受推崇的宏觀視野移開,不在世界史的結構下觀察臺灣,單純從島上原住民的角度來思考——
在所有外來者未到之先,臺灣島上居民如何理解自己的世界?




1
島民自述起源
讓我們先定位到太平洋上的一組座標:北緯 22°02'、東經 121°33'——
這裡是一座蓊鬱小島,安躺於西太平洋強勁的黑潮邊緣。島上居民稱之為達悟人之島(Pongso no Tao),地圖上,通常被標示為「蘭嶼」。
達悟人之島很小,面積約 46 平方公里,島上火山散落,只在沿岸有可供利用的平地,也是達悟人聚落所在。今天的環島道路全長約 37 公里,開車環島只要一兩個小時,就算在沒有公路也沒有汽車的過去,也能在一天內步行走完全程。總之,不可能住在這裡卻不知道自己棲身於大洋小嶼。
達悟人之島西邊約 70 公里還有一座島嶼,地圖上標記為「臺灣」,相比之下是非常大的島,兩者面積比約為 1:790。若把達悟人之島想像成一枚郵票,臺灣就約當一個中等大小的玄關腳踏墊。在世界地圖上數算,臺灣是全球第 39 大島,居住在這麼大的島上,就不見得能像達悟人那樣,清楚意識到自己是島民。不是每個臺灣原住民族的語彙裡都有「島」這個字,恰好說明了這一點。

1933 年日本政府繪製的〈紅頭嶼略圖〉。紅頭嶼為蘭嶼舊稱,從地圖右上方可見臺灣本島與紅頭嶼間的地理位置關係,也可看出臺灣和蘭嶼的面積比差異。
圍繞臺灣島原住民的謎團不少,但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——和棲身汪洋小嶼的達悟人不同,臺灣島上的原住民似乎都不是遠洋航海的民族。
或許是因為長久以來,島民的對外活動被西側陰晴不定的海域(臺灣海峽)和東方寬廣強勁的洋流(黑潮)所限制。又或許單純因為臺灣是個大而富饒的島嶼,能夠滿足許多人群在島上自給生活。
這些人群現在被稱為「南島語族」,是日本統治初期以語言而非人的親緣所做的分類。基因研究顯示臺灣島上的原住民族沒有單一共同的起源,也無從推知各個群體長時間內如何遷徙分布。不過,撇開科學研究,臺灣原住民又怎麼解釋自己的起源?





2
島民與環境的互動
除了時間觀,原住民族視野中的世界又是什麼樣子?
我們不妨從原住民族眼中的自然和動植物等具體事物開始。人類學者謝世忠曾就泰雅、布農、阿美的命名慣習來探討三個民族與動物的關係,在不刻意計入亞群和地域差別的原則下歸納出如下圖像:
儘管這一圖像十分有趣,卻忽略原住民族傳統上並沒有將某些東西歸類為動物、某些東西屬於植物,進而統合在一個生物學分類樹下的思考。原住民看待周遭的一切,從石頭到樹木到昆蟲到走獸,其實都是一對一的、個別的關係。
以動物來說,各族語言中最接近「動物」的統稱性詞彙大概是「獵物」,但並非所有動物都是獵物,那些不屬於獵物的動物可能有名字,也可能沒有名字。取名與否,往往反映原住民族與這些動物的互動與關係疏密。
原住民族的知識與生活經驗高度相關,在不同的族群之間,看似相同的傳說與習俗也有所差異。
以
「紅嘴黑鵯」為例,泰雅族認為這種名為 sabin 的鳥曾以嘴和爪折斷樹枝,協助撲滅森林大火;布農族和鄒族也有類似的傳說,且彼此可相印證,大意是布農與鄒的祖先在玉山頂上避水,沒有火種,無法煮食取暖,其他動物幫忙去取火種都失敗了,最後是紅嘴黑鵯(布農稱為 haipis,鄒稱為 uhngu)成功帶回火種。
這些與動植物有關的傳說故事,是外界認識原住民文化的敘事起點,但外人也很容易忽略,傳說故事也有位階或效力的區別。例如泰雅族關於紅嘴黑鵯的故事,本質上是以傳說解釋外在事物的樣貌,布農與鄒的故事雖然也以火燒來解釋紅嘴黑鵯全身黑羽、紅喙紅爪的由來,但因為「洪水傳說」與「祖源」相牽連,在這樣的故事裡出現的紅嘴黑鵯,自然在族人心中占有特殊地位。
原住民族本是高度仰賴環境資源的自給人群,因此知識必與群體生存息息相關,迥異於講究分辨物種「本質」的當代科學體系。這點除了體現在取名與否,也體現於名稱的細緻程度。
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,這些命名的樣態似乎雜亂難解,因而更突顯原住民傳統上對世界的認識迥異於現代社會。
那麼,涵容一切的地理空間本身,在島民眼中又是如何?





3
島、島民與空間
角板山 Hapun 社的原住民。
我們生活在現代主權國家,傾向於認為所有的文化群體都有類似「領土」的概念。但臺灣原住民認識空間的方式與現代國家不一樣,我們無法就每個原住民族畫出國家行政區劃般的地圖,大家常見的臺灣原住民族分布圖,只是概示各民族的生活與活動範圍。
一般而言,原住民的領域觀念是從家、氏族或部落等群體出發,再延伸到獵場,以及群體之間的緩衝區。但各個民族看待、利用空間的方式不盡相同。舉例來說,鄒族的社會和空間都以大社(hosa)為核心,並有小社(denohiu)為其外圍,具有防禦作用,構成一個「類似領土」的空間。
其他民族的領域結構沒有鄒族那麼清晰,通常又因血緣、語言、風俗的異同而結成子群,例如布農、排灣、魯凱、卑南、賽夏族等。此外,還有一些人群具有更強烈的部落中心或部族傾向,而非抱有今日習見的「民族」概念。例如泰雅族和阿美族,兩者的生活空間差異極大,前者在山區各個流域,後者在平地或海岸地帶,但都以部落為基本社會單元(泰雅族稱為 galang,阿美族稱為 niyaro’)。
透過這些舉例可以知道,概述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與文化是相當困難的作業,因為各民族的歧異度極高,不論從哪個方面都難以概論。更有甚者,外部觀察者往往想當然耳,將自己的知識體系套用在原住民族身上,導致觀察失焦。
近年來有些反省認為,將臺灣原住民以部族、地域區分而個別論述,觀點有欠統合。但從以上簡述的各族差異看來,統合性論述往往必須以丟失文化脈絡為代價。再者,原住民經歷大清帝國、大日本帝國乃至中華民國的殖民,殖民者的民族學分類如今是原住民社會的既成現實,且各個民族與外人和國家的往來經驗各不相同,有的平順,有的慘烈,維持原住民自我認識的單元為理解的基礎,可能還更切合當代原住民的認同和經驗。
原住民各族的差異極大,若我們還是想試談原住民族視角下的原住民族歷史,可以從何處著手呢?由於篇幅有限,我們無法細論所有民族,以下只舉兩例來說明發展原住民族觀點之原住民族史的可能起點。




4
口傳與文字共構真實
1952 年拍攝的賽夏族矮靈祭影像。
據說許久以前,賽夏族曾與一群矮人(Ta’ay)比鄰而居。矮人很矮,農耕與巫術高明,賽夏族從矮人獲益匪淺,但後來兩群人發生嫌隙,賽夏族在矮人必經的獨木橋上動了手腳,導致矮人摔落谷底,只有極少數人倖免。矮人已無法繁衍後代,離去前教導賽夏族一套繁複的祭儀,命賽夏族定期舉行,才能免於災禍
以上是賽夏矮靈祭(paSta’ay)的由來。這是臺灣最出名的原住民祭典之一,你可能早有聽聞,或許也好奇臺灣島上是否曾有矮人存在,但你可能不知道,這個話題並沒有表面看來那麼簡單。
賽夏族不是島上唯一有矮人傳說的民族。2015 年一項綜觀臺灣原住民族矮人傳說的研究,歸納出如下的三個「矮人傳說圈」:
各族群與矮人的關係不盡相同,不過大家形容的矮人倒很相似——矮人很矮,膚色很深,力氣很大,巫術很高。外人或許因為這些故事頗多相通,而抱有「說不定這些傳說某程度上反映真實」的想法,但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考慮,臺灣曾有矮人,是毫無疑問、絕對可靠的事實。這不是因為各族傳說可以交互印證,也不是因為賽夏矮靈祭的內容極為詳細,應該並非胡編亂造,而是因為賽夏人在祭典上表述他們與矮人交往、交惡、設計、殺戮、被詛咒、開始舉行祭典的完整過程。
如果有一天,我們要有意識地展開臺灣原住民史的書寫,矮人的消失可能是一個理想的起點。
以此開始的原住民史,想來將不再以線性的數學時間作為書寫的順序,也不以與外部世界的交往為重要性的衡量標準,而是依循原住民口述傳統的精神來判斷何者重要,同時又不排斥臺灣作為文字社會的現況。





5
口傳社會與
文字史料積極互動
文字史料積極互動
《馬尼拉手稿》又稱《謨區查抄本》(Códice Boxer),為1590年代的西班牙文獻,一共收錄70餘幅彩圖,記錄了當時包含臺灣在內東亞各族群的風俗。
不久便有約二十名異教徒向我們接近。他們赤身裸體,像加納利群島人那樣,僅以腰布遮羞。他們披頭散髮,有些髮長及耳。他們當中有些人戴著狀似王冠的白紙條。他們所有人都帶著弓和許多箭,都有長而尖利的箭頭。
“
”
1582 年 7 月,一艘載有近三百名乘客的戎克船從媽港(澳門)啟航前往日本,途中遭遇暴風雨,擱淺在一座島上。根據船上三名耶穌會士事後寄出的書信看來,他們擱淺的島嶼必是臺灣無疑。耶穌會士 Alonso Sánchez 信中寫道,從媽港往日本航程中「有一島嶼,由海上可見她高大青翠的山巒,因而獲得 Hermosa(美麗)之名。葡萄牙人航往日本,在這島嶼和中國沿海間往來,已有四十年之久,卻從未登岸或探索過」。
這艘搭載近三百人的戎克船在船難中解體,倖存者上岸後,一邊要面對島上原住民的攻擊,一邊要打造新船,辛苦了近三個月,終於在 9 月底駕著新船離開,八天後返抵媽港。
這可能是西方世界與臺灣島上原住民的接觸首次見諸文字紀錄,臺灣史研究者對這次船難地點各有推測,以主張北臺灣淡水河口者居多,但也有主張中臺灣者,此外,邱馨慧綜合書信中的描述,判斷船難可能發生在南部大員灣,他們遇上的很可能是西拉雅人。無論哪一種推測為真,最後這一看法對於西拉雅人來說,毋寧具有相當的吸引力。
西拉雅雖然還在為法律上的原住民族地位努力,但在「原住民口述傳統」和「外來者書寫的歷史」這方面,西拉雅與其他原住民族相比,確實佔有獨特的地位。





19 世紀蘇格蘭攝影師約翰・湯姆生所拍攝的西拉雅族肖像。
Ka assi nein ni-kalang tou kidi-appa k'anna ka iroua ta vaha ka yrrang, ka nimæeu-ymmid mæeu-mia neini-æn.(不知不覺洪水來了,把他們全都沖去。)
“
”
值得附帶一提的是,臺灣原住民族雖然傳統上都是口述社會,但在現代化、文字化之前,已經對文字有一定的經驗。例如阿美族人傳說,祖先本來有文字,只是不慎掉入水中而失去了。布農族也有類似的傳說,且文字丟失於大洪水時代。
這類傳說細究起來很有意思,暗示臺灣原住民族有更多與文字社會成員遭遇、往來的經驗。只是到目前為止,這類傳說不受重視,也不曾被人提出討論。說不定在西拉雅領路之下,其他民族也能以各自的傳說為立基,展開史觀建構、歷史書寫的旅程。